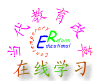|
2.从学校课程管理的权责分配来看,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行政权力主体各司其职 在原先的中央集权课程管理体制下,不单是地方和学校缺乏明确指定的课程管理权责,连国家一级的管理权责有哪些也不甚明了。实行新的课程管理体制后,三级行政主体的管理权责得以明确。就课程管理权责的具体分配而言,国家主要是负责制订国家课程计划、国家课程的课程标准,并对依据这一标准编写的教科书进行审定;制订国家课程实施的指导性意见,以及地方一级和学校一级课程管理的基本规范;确定课程评价制度,监控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整体运行质量。地方的主要权责是制订本地实施国家课程计划的方案,以及制订地方课程计划,开发地方课程,指导校本课程开发,并对中小学的课程实施进行指导、监控和评估。学校是所有课程得以真正实施的地方,其课程管理的权责可概括为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有效实施,以及校本课程的合理开发两层基本含义,包括课程计划管理、教学管理、教材选用和开发管理、课程评价管理、校本课程开发的管理以及课程管理的保障等内容。由此可见,尽管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构成的学校课程整体中,是以国家课程为主,但管理学校课程是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行政权力主体的共同责任,只是它们承担的职责各有侧重,范围有所不同罢了,不能归结为什么课程由谁开发由谁管理的问题。 3.从参与课程决策与开发的角色来看,学科专家主宰走向各种有关人士分权 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所带来的课程权力的重新分配不单出现在教育行政体系内,而且发生于课程改革不同层面的不同范畴的不同角色之间。以往的课程开发由中央政府授权给学科专家代理,导致“间接或直接有关人士”(Indirect or direct stakeholders)在课程改革中的“缺席”。且不说教师没有像医生开处方那样的课程自主权,学生没有课程的选择权,家长作为“消费者”对学校课程没有知情权、建议权和评价权,就连课程论专家都无处寻觅。实行新的课程管理体制后,除了中央教育官员、学科专家这些传统角色外,地方教育行政人员、课程论专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代表、工商企业界的人士等等,都在或鼓励他们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课程开发和课程变革的过程中来。这无疑有助于课程科学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