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三节 法与科学技术的相互作用
|
|
| 一、科学技术对法的影响 尽管如前所述,科学和技术不可相互混淆,但我们仍然倾向于在此将科学和技术对法律的影响合起来加以论述。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与法的关系所以会进入当代法理学的研究视野,与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的密切结合以及二者的充分社会化密切相关。与近代以前科学与技术分离的传统不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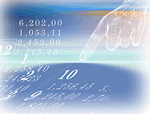 |
| 近现代以来,技术进步更多仰仗于科学,科学也更多借助于技术:在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中会出现令人惊异的应用上的特征,在应用研究的范围内则发生了理论上的突破。①与此相应,无论科学抑或技术影响法的方式都不再那么纯粹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分别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各自独有的意义和影响。 (一)法的产生和发展以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为一般基础 法是人类对自身行为及其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的规则体系,这样一种调整机制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乃至体系化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由自发到自觉并不断系统化的过程。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理性、自觉、系统的科学认识,是法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基础。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文字的产生,使得习惯法的记载乃至严格意义的成文法的产生成为可能。印刷术的发明,造纸业的发展,导致成文法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的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更令法的形式、结构、信息传递方式、法典编纂方式发生变革和发展。 (二)法的理性化、形式化和技术化借助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渗透性影响 第一,根本上说,法和科学都产生于人类理性和经验,是人类理性和经验的产物。但是,法的理性和实证特性更多地借助于科学的影响,并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实证科学未获充分发展、科学发展水平较低的近代以前,法律更多地具有神权法色彩,理性、逻辑、实证和经验的成分都很缺乏。如对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借助天意、偶然因素或者虚构;对责任的追究常常借助神判或者决斗。而在近现代,随着实证科学和相应技术的发展,由数学逻辑和实验观察所支撑的理性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延伸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法律的制度和程序设计。法律规则的普遍、客观、确定、合逻辑等属性,司法中事实认定的严谨求实,推理和判断的客观、理性、实证、逻辑严密、理由充分等形式合理性要求,都借助和受益于科学的理性与实证精神。”从而使法更多地摆脱偶然性、任意性、随意性因素,成为能为人的理性所把握、预测和控制的理性结构。 当然,法律上的理性和实证与科学上的理性和实证仍是有差别的,这主要是由于法律所面对的是难以复制和不具可逆性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因而,纯粹的数学和逻辑推演以及在给定条件下可重复进行的观察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法律:法律领域中科学方法的运用也应是有限的,否则可能导致民主操作机制的僵化或不合时宜。 第二,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法必须是统一、普遍和可操作的,而事实上,法只有被形式化、技术化之后才可能是统一的、标准化的、可操作的,不能形式化、技术化、程式化的东西往往难以统一和操作。在近现代,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高度社会化的状态,有着比以往更强烈的社会管理的技术化追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的趋势导致技术的工具理性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和介入,使政治和社会生活纳入到技术的合理性控制之下。近现代西方法的形式理性乃至形式法治也正是借助技术理性的深刻影响发育形成的。法的一般、抽象、普遍、明晰、准确、可预测、无例外地非区别对待、注重功用、效益和过程的程序性,以及法的表达形式、结构、语言上的技术要求等,都可以从技术理性对法律理性的介入和渗透中获得解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