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郭沫若翻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封面 |
"五四"时期,郭沫若不仅以他的,新诗创作揭开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的一页,同时,在戏剧,小说乃至散文的创作上,也以其积极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见称,使他早期便成为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
一、 郭沫若的早期剧作--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意表达
(一)诗剧"女神三部曲"
郭沫若的剧作,同他的新诗一样,也是发轫于五四时期。在莎士比亚,歌德等剧作的影响下,于1920年便连续写下了《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即女神三部曲)等三篇诗剧。这些诗剧,同《女神》中时许多诗篇一样,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深刻的思想认识,鼓舞和启迪了广大中国青年。
|
《女神之再生》 :取材于上古共工与颛顼争帝和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诗剧中的共工和颛顼,为了当元首,做皇帝,不惜驱使"党徒"互相残杀,只闹得天体破裂、尸骸盈野,飞沙走石,一片昏暗。借此,诗人强烈诅咒了现实社会军阀混战的罪恶。揭示了人民在军阀战争中命运的悲惨和对这种不义战争的憎恨。诗人要建设一个--美的中国。诗中的女神,自然是诗人极力歌颂的"美的中国"的创造者。诗人把传说中的"补天"改写成为再造,主张"破了的天体"要"尽他破坏不用再补","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标志了诗人当时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五四时期的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
《湘累》 :取材于屈原的故事,这里写的只是屈原被放逐后与女须乘船游洞庭湖的生活片断。诗剧的主角屈原,强烈申诉了被放逐的不平和郁愤,抒发了怀念故乡、忧国忧民的深沉的爱国激情。但是,尽管"这个混浊的世界"把凤凰说成鸡,把麒麟说成驴马,并用"疯子"名目罩住他,借以把他的"美洁莲佩扯去",把他的"高岌的危冠折毁",并"投些粪土"来攻击他,他却仍然不做"送往迎来的娼妇",更不愿用自己的如同生命一样的诗,来赞美陷害自己的浊物--郑袖那样的人。在这里,诗人所赞颂的屈原对于祖国的怀念和忧虑,以及对于那"混浊的世界"的控诉,正是诗人自己在五四时期的"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的喷发,屈原的那种强调自由创造和自我表现的精神以及气吞山河的气魄,更是诗人在五四时期火山爆发式的觉醒意识的狂热表现。因此,诗人后来说"《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
《棠棣之花》 是三篇诗剧中较为重要的一篇。其中,不仅诗人的爱国主义表现得更为具体,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了诗人思想认识的高度。诗剧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侠累的故事。所写的,只是聂政与姐姐聂莹在母墓前诀别的情景。历史故事中的聂氏姐弟的思想,本来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的思想。但诗人却充分利用了他创作上的"自由",加以改造和升华,使他们具有了为祖国和人民而献身的英雄怀抱。他们对连年战争,表现了切肤之恨。因此,他们悲壮地表示:
不愿久偷生,/ 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 救彼苍生起!
诗剧结尾的歌辞:
去吧,二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进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在这里,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取得了完美的结合。实际上,这正是诗人自己的"报国济民"的英雄怀抱。
(二)诗剧《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
1922年,郭沫若创作了《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两篇诗剧。这两篇诗剧,前者是对月宫中的"极乐世界的憧憬,后者是对离群索居的"自由纯洁的原人"生活的渴慕。两者都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但他仰慕的是大海,星空和太古,追怀的是月宫的圣洁和明净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节操,"浓厚地带着虚无主义色彩。"
戏剧原本是诗的一种,而作者又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因此,他的戏剧创作,在西欧的几位剧诗人影响下,从诗剧开始,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他的处女作《女神三部曲》,也可以说是他以后大量史剧创作的滥觞,在题材,思想和艺术上作了必要的准备。但《女神三部曲》,或因通篇押韵,或因抒情有余,而情节的波浪起伏不足,便很难搬上舞台,只能为案头作品。《广寒官》比较注意了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到了《三个叛逆的女性》便步入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比较娴熟的阶段。
|

郭沫若翻译的《约翰·沁弧戏曲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三)早期戏剧代表作--《三个叛逆的女性》
1923年2月和7月,他先后写成了多幕剧《卓文君》和《王昭君》,1925年6月,又写成《聂莹》,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于1926年出版。在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浪潮启迪下,作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道德对广大妇女的束缚和蹂躏的严重性。因此他便大声疾呼:"我们如果要救济中国,不得不彻底解放女性,我们如果要解放女性,那么反对"三从"的"三不从"的道德,不是应该提倡的吗?"所谓"三不从",就是与"男性中心"的封建道德相对,提倡"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
《卓文君》:便是"三不从"的标本,做的是翻案文章。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历来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大逆不道"和"有伤风化"。某些文人墨客,也曾把它当作风流韵事,述诸笔墨,"但每每以游戏出之","供自己潦倒的资料"。而剧本《卓文君》却反历史的偏见,正面歌颂了卓文君蔑视"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和为争取人格独立,婚姻自主而勇敢投奔司马相如的反抗叛逆精神。作品还着意揭露了两个封建卫道士卓王孙的势力眼和程郑的卑鄙无耻。两相对比,更显示了叛逆者的高洁。特别是当夜奔司马相如的事情败露后,作品借历史的亡灵,以卓文君在父亲和公公的辱骂和威逼下的慷慨陈词,痛快淋漓地喊出了五四时代力图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广大青年妇女的心声。所以,当剧本发表后,立刻得到了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女学生的欢迎和赞扬,并把它搬上了舞台。但同时,也遭到了封建卫道者的责难,甚至在县议会和省教育会讨论决议禁演此剧。这便从反面显示了此剧的重大社会影响。
《王昭君》:如果说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显示了"在家不必从父"的反封建意义,那么剧本《王昭君》中的王昭君下嫁匈奴,则又是"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而这"夫"。又不是凡人,乃是皇帝,这就使得《王昭君》剧本比起《卓文君》来,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反封建意义。
在传统的戏曲和诗词中,都是把昭君出塞写成命运的悲剧;是由于画师的罪责和君王的误选,造成了昭君的不幸。而郭沫若则一反这种陈腐的观点,把昭君出塞写成了"性格的悲剧"。王昭君的下嫁匈奴,是出于"彻底反抗王权"。于是便把一个充满哀怨情怀的王昭君,写成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叛徒。她对"入选进宫"并不感到荣耀和幸福。也不象其他"后宫佳丽"那样去贿赂画师以争宠于皇帝。对于爱财贪色的画师毛延寿的威逼和敲诈,给以严词拒绝。这便初步反映了她的视荣华如粪土和反抗强暴的性格。当汉元帝知道了画师的欺骗,倾倒于昭君的美丽,决定另换一宫女下嫁匈奴,并要册封昭君为皇后时,昭君非但对皇上的宠爱和垂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给以极度蔑视,公开对抗皇上的意旨,自愿"投荒",并且当面控诉了汉元帝的恣肄威虐、骄奢淫逸的罪行。在这里,便充分地表现了王昭君的不为荣华所动和不为王权的淫威所屈的高洁品格和反抗叛逆精神。
在封建社会,在迫害蹂躏妇女方面,王权可以说是夫权的最高表现。因此,王昭君对汉元帝的反抗斗争的描写,在思想上便具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反封建意义,它会更使人清楚看到封建制度将妇女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的罪恶现实。
《聂莹》:在《三个叛逆的女性》中,《聂莹》可以说是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高峰的标志。因为这部作品,不仅有其反封建的用意,而且从现实斗争出发,有着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
《聂莹》写的是聂政刺杀了韩哀侯和韩相侠累而毁面剖腹自杀之后,姐姐聂莹,为传播弟弟的"侠情义气"为弟弟全节、前往韩市、认尸自杀的一段。所以,《聂莹》乃是五年前的诗剧《棠棣之花》的续篇。
作者在《写在<三个叛逆 的女性>后面》一文中说:"女性的彻底解放须得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之后才能办到。女性是受着两重的压迫的,她们经过了性的斗争之后,还要来和无产的男性们同上阶级斗争的战线。基于这种思想认识而写下的《聂莹》,就比两年前以反对"三从"为基点的《卓文君》和《王昭君》表现出了更新的思想高度。聂莹的反抗叛逆,己不仅止于对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而是反对反动统治者的专横暴虐,压榨百姓,制造战争和涂炭生灵,她要以自己的死来警醒人民起来去除尽天下的王和宰相,以求得大多数人的平等、自由和解放。
作者还曾说:"没有五卅惨案的时候,我的《聂莹》的悲剧不会发生",它是这次惨案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剧本的创作动因直接来源于激烈的现实斗争,所以剧本刚刚写好,就被上海美专拿去排练演出了,不仅以七百多元的收入支援了罢工的工友,而且及时地发挥了它鼓舞战斗的作用。
(四)早期历史剧的艺术特色
首先,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 。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是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也是许多志士仁人追求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时代,他看重与采取的正是那种求进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要重视和张扬这种精神去反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去推动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
其次,独特的"史剧观念" ,并形成了突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性。郭所实践的是所谓"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又容许出于主题的需要的自由虚构和改造。作者并不遵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原则,而是运用过去一贯主张和使用的"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的浪漫主义方法,给历史题材以新的创造。剧中不但有许多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就是对主要人物的刻划,也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升华,把作者自己和所处时代的革命精神,"吹嘘"到古人的骸骨中去,使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这便为他以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道路。
再次,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 。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艺术个性。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表现了自己。郭沫若的历史剧之所以比同时期的历史剧更有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剧中大胆地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与个性。
最后,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浓郁的诗意,成为戏剧的诗 。剧中经常穿插些抒情歌曲、优美的琴声,剧作增加了浓郁的诗味,加之人物的动作、对话,告白乃至场景的诗化说明,使剧作显得诗意葱茏,优美动人。因此,他的剧作,如他自己所说:"广义的来说吧,……确实是诗。"他抗战时期创作的许多剧本(《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都曾延续和发扬了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历史上看,戏剧本是诗的一种,我国传统戏剧也无不以白为宾,以曲为主,唱词中有很多好诗。"五四"以来的现代话剧,在形式上接受欧洲近代散文剧的影响,人物对话采用散文,不用诗体。"五四"初期一部分话剧作品(如田汉的早期剧作与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尚保持浓郁的诗意,但在第二个十年社会剧的大发展中,话剧的抒情性就大大减弱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曹禺的《北京人》、《家》及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历史剧为代表,将诗、剧融合的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诗。
二、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创作--浪漫主义"自叙传"抒情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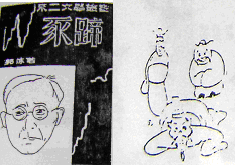
1936年不二书店出版的郭沫若小说集
《蹄》及《秦始皇将死》插画 |
(一)作品集及创作主题
作品: 郭沫若前期的小说除中篇《落叶》外大都收入《塔》(小说戏曲集),《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橄榄》(小说散文集)中。
《牧羊哀话》是郭沫若最早发表的一篇小说,作品以朝鲜为背景,体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创作主题: 以诗意葱容的笔法,表达追求个性解放和美好爱情的主题。
思想内容:1、刻意表现自我对爱情的追求及潜意识的流露。 《残春》、《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
《落叶》 中篇小说,为纪念他与自己妻子的坚贞的恋爱生活而写,具有较为深刻的反封建意义,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 等篇章也描写爱情生活。前者是写叔嫂间的爱恋,后者中的主人公,是既爱着自己贤惠的妻子,又去狂热地追求一个卖甜食的姑娘。这两篇作品对人物潜意识的刻画十分深入。
|
2、以个人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自传体散文式小说 。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上的困窘和生活的悲惨。《漂流三部曲》、《行路难》。
《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是自叙传类的小说,小说中的爱牟(英文AM音译)实际上就是郭沫若自己,作品记叙和描述了郭沫若留学日本和从日本回到上海办刊物期间的生活。
《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十字架》等三个短篇 。这是根据作者一九二三年春回国后到一九二四年再去日本前的一段生活经历写成的。
《歧路》是写他怀着朦胧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带着妻子从日本回国后,同志趣一致的友人合办一种文学杂志。但在这种文墨生涯中,非但使他看不到改造社会的效用,而且文学是不值一钱的,连自己的妻儿都养活不了。无奈,只得将妻儿送回日本,使其自谋生路。
《炼狱》写他为了排解妻儿走后的孤寂而同友人去太湖游览的情景。但狂饮大醉,情绪一蹶不振,太湖的胜景,仍然医治不了他内心的苦痛,只得仍受上海斗室中"炼狱"一样的生活的煎熬。
《十字架》中,他的情绪便又见起色,他辞退了四川C城红十字会的邀请,痛快地用脚践踏了作为聘金的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并激愤地说:"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他决定到日本去。
《行路难》是《漂流三部曲》的续篇,小说分上,中、下三篇 ,写的是爱牟在一九二四年四月间重到日本与妻儿团聚后的窘迫、困苦的生活。小说以爱牟一家从福岗迁居佐贺山中为线索,通过退房子、处理家具、坐火车、找房子等情节,表现作为一个穷苦知识分子的爱牟,在日本那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见欺于日本人和有钱的商人,而饱受凌辱、处处碰壁的困境。
(二)早期小说创作的艺术特点
郭沫若的小说语言流畅,感情丰富,有的作品具有辛辣讽刺的笔调。但他的小说数量较少,结构有些不太严谨,有些抒情过于夸张,少含蓄意味,成就不如他的诗歌和历史剧。
[知识点]
《女神》的产生和影响、泛神论、自由体诗、《瓶》、《三个叛逆的女性》、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六个历史剧、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原则。 [思考题]
(1)试论郭沫若《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2)简评泛神论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并说明郭诗如何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特征。
(3)就郭沫若的《天狗》(或《凤凰涅盘》)写一篇赏析短文。
(4)简论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艺术特色。 [必读作品与文献]
《凤凰涅架》、《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
《夜步十里松原》、《天狗》、《太阳礼赞》、《瓶·第十六首:春莺曲》
《瓶·第三十七首》、《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屈原〉、〈论诗三札〉
《我的作诗经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评论节录]
温儒敏:《郭沫若其人其诗》
邹羽:《批判与抒情》
姜铮:《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
王文英:《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