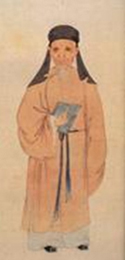| 上一章 | 下一章 |
|
明清易代,满族入主中原,君临天下,屠城、圈地、薙发等一系列暴戾强加行为,激发了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传统的“夷夏之防”一类的观念受到重视。顾炎武以辨析“亡国”与“亡天下”,抒发和表达了相应的感受和认识。他认为世上有两种大的灭亡:“亡国”、“亡天下”。仅仅是改朝换代,叫作“亡国”,若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就叫作“亡天下”;面临“亡国”之险,其君其臣责无旁贷,面临“亡天下”之险,即使卑贱如匹夫,也应承担挽救之责。因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可以看出,顾炎武民族意识和情感的背后,有一个起支撑作用的价值观念,即天下应该是仁义道德流行的天下,天下应该是天下人的天下。
社会政治思想。从顺治10年开始,黄宗羲历经10年时间,撰成《明夷待访录》21篇,“明夷”为《周易》中一卦之名,其象为太阳入于地中,“晦其明也”,其意为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意志不衰。故此书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此书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就其核心思想看,集中体现了黄宗羲对皇权专制制度的批判。 黄宗羲从维护“天下之利”的民本主义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君权”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命题。他肯定天下人皆有其“私”,这是人的天然本性,皆当合理维护,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痛斥君主“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弹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以供我一人之淫乐”,“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做法,揭露专制君主利用皇权,“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成天下之大公”的强横、虚伪,认为专制皇权侵害了天下人的正当合理的利益,遭受了无君主时代所没有的痛楚和灾难。在君臣关系上,他批判了“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认为设君设臣原本是使其负责天下人的事务,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其治理天下的状态,仿佛抬运大的木头,君臣相互唱和,共为抬木头的人。臣不是也不应该是为君主一人服务的,即“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合理的专制皇权能肆无忌惮地运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维护专职皇权的法律。所以,黄宗羲又对这种法律展开批判。他分析历史,得出一个结论,即“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认为三代以后的法律,不是“天下之法”,而是“一人之法”,这种法律的特点是,“藏天下于筐箧”,千方百计束缚天下臣民,以维护皇权的独尊、独治。黄宗羲认识到制定符合天下人整体利益的“天下之法”的重要性,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其意是说,制定体现天下人意志、维护天下人权益的法律,才会造就出以维护天下人正当利益为宗旨、为怀抱的“治人”,也才能把维护天下人利益的观念真正落实。 黄宗羲探寻着改善君臣关系、限制君主权力、维护天下人正当利益的政治道路,他把眼光头投向古代,和顾炎武相类,也欲化腐朽为神奇,借古方以医今病。他将古代的学校制度和明代东林党人的政治抗议行为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古代的学校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培养士人,还在于主持天下之舆论是非,使天子不能也不敢自以为是非。如此,学校就具有的了议政、平天下是非的职能。应当指出,黄宗羲对学校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更主要的是其理想的政治境界与法古视野相融合的结果。他要以学校主持天下之是非,除了为政治寻求出路,还有为明末东林党人政治抗议合理性辩护的用意在。他亲见身为东林党人的父亲黄尊素因政治抗议,为阉党害死,他本人参加了接武东林的“复社”,因打击阉党险遭不测。这些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很自然地融入批判腐朽黑暗政治、阐发政治理想的过程中。 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顾炎武读罢其著作后,精神为之一振,在给黄宗羲的信中由衷地赞叹道:“大作《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为了配合变法运动,将《明夷待访录》大量秘密刊印、传播,以觉醒民本和民权意识,以增强维新变法的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黄宗羲的哲学思想体现于对于理学、心学的反省和批判方面。他主张“盈天地之间皆气”的观点,认为生人、万物皆由气化而成。化生万物的气,是万物的本原,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为无限。至于理气关系,他认同其师刘宗周的“离气无理”的观点,坚持“理为气之理”,反对“理无先后之分”说,以及“理先气后”“理为气本”的观点,指出,“沉浮升降者”为气,就“沉浮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为理,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在道器关系上,他认为,“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 而无所谓理”,“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体现出“道寓器中”的本体论和“即器明道”的认识论。在心性问题上,他反对以性为体、以心为用的观点,主张心为体,性为用。他还以气本论为武器,对鬼神迷信、方术以及佛教轮回之说展开批判,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的思想倾向。 |